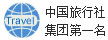關(guān)于麗江古城無城墻,民間傳說是因土司姓木,木字加框成“困”字不吉,故不修城墻云云。筆者以為需分開來說。
一是古城始建于寧末元初,它是在原始村落的基礎(chǔ)上發(fā)展起來的,而土司姓木是明朝的事,說明麗江城本來就沒有城墻。二是木氏進(jìn)城后,忌諱“困”字而不修城墻,說明納西統(tǒng)治者能從民族生存與發(fā)展考慮,趨利避“困”,順應(yīng)了歷史發(fā)展的潮流,這是應(yīng)當(dāng)肯定的。三是納西族本來是從游牧民族了展起來的地,無論民眾還是統(tǒng)領(lǐng),在文化意識(shí)上都缺少城墻觀念。在土司末姓木之前,他們?cè)?a href="/guide/baisha.htm" target="_blank" title="白沙旅游">白沙的城成沒有城墻。按納西族學(xué)者和中孚先生的話說:一個(gè)把大地作為驅(qū)馳之地的民族,怎么會(huì)用幾塊磚頭,幾條淺溝去護(hù)衛(wèi)自己、約束自己呢?
所以,納西族不設(shè)城墻是一種源于游牧民族的,無拘無束的,無所畏懼的、開放吸納的精神氣質(zhì)的體現(xiàn)。據(jù)說康熙皇帝是中國(guó)歷史上唯一不修長(zhǎng)城的帝王,他認(rèn)為長(zhǎng)城并不是最好的屏障,只有國(guó)富民強(qiáng),修德筑仁,萬眾一心,才能“眾志成城”。這是開明君主的思想,也是游牧民族開闊胸襟的真實(shí)寫照。
木氏的衰亡本是社會(huì)發(fā)展的必然結(jié)果,不幸的是,清朝統(tǒng)治者把“革命”的目標(biāo)擴(kuò)大到納西社會(huì)的所有上層建筑領(lǐng)域,納西人甚至被剝奪了做武士的權(quán)利。男人們,特別是城里的男人們,變成一群游手好閑,無所事事的人。有的抽上了鴉片,資財(cái)耗盡,體質(zhì)虛弱;有的養(yǎng)些花鳥蟲魚,玩點(diǎn)棋琴書畫,在祖先們?cè)紶柹娅C的文藝領(lǐng)域,喝杯清茶,作些小詞,聊以度日;有的躺在樹蔭底下,講幾個(gè)《三國(guó)》、《列國(guó)》的故事。木土司本人也曾任“大研古樂隊(duì)的總監(jiān)”,與一些情趣相投的樂友們陶醉在唐詩(shī)宋詞所營(yíng)造的傷感國(guó)度里。于是,納西族變成一個(gè)“文化的民族”;納西音樂也變成一種“哀傷的音樂”。到清朝咸、同年間,杜文秀起義的洪峰波及麗江,木府毀于兵火,一座集中了納西族、白族、漢族等能工巧心血和汗水的建筑精品毀于一旦。雖然戰(zhàn)后又重新修建,但以清朝每況愈下的末世土司的實(shí)力,已無力恢復(fù)盛明時(shí)代木府建筑的巍峨與壯觀。
正是,落花流水春去也,天上,人間。
麗江古城無城墻之謎
相關(guān)閱讀:
- 金秋旅游好去處 云南麗江風(fēng)韻足2011/11/15
- 云南麗江旅游景點(diǎn)介紹2010/11/11
- 云南麗江旅游住宿須知2010/11/11
- 云南麗江美食攻略2010/8/18
- 云南麗江客棧詳細(xì)介紹2010/7/16
- 云南麗江購(gòu)物指南2010/7/16
- 云南麗江美食攻略2010/7/16
- 云南麗江酒吧推薦2010/7/16
麗江旅游景點(diǎn)大全查看所有麗江景點(diǎn)
 麗江古城
麗江古城 玉龍雪山
玉龍雪山 長(zhǎng)江第一灣
長(zhǎng)江第一灣 觀音峽
觀音峽 老君山
老君山 白水河
白水河